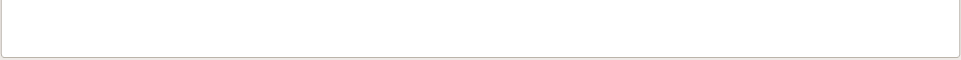乐器是文化的载体,一种乐器凝聚着一种文化的特质。闵惠芬二胡声腔化的本质,是开启了现代二胡的寻根之路,为二胡寻找那原本属于它的文化母体——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……
文|岳峰
三年前的初春,在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,我与闵惠芬老师相遇。席间,当聊起“器乐演奏声腔化”的话题时,闵老师提到了她的一张新近之作——二胡CD《凤吟》,对其中的演奏、配器、乐队与指挥,抑或录音、合成及后期制作都十分满意,可谓是心仪之曲。几天后,托人转送了一盘与我。
带着某种期待,播放了这盒封面上隐现着一只仰天长歌的凤凰画面的二胡光盘。渐渐地,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悲凉和凄然:一只琵琶轻拢慢抹的引奏之下,悲声低诉的二 胡从弓弦间哀婉流出:“我今独抱琵琶望,尽把哀音诉,叹息别故乡,唉!悲歌一曲寄声入汉邦。”胡声琴语,句句慢,声声断;低眉惆怅,举目茫然;活现出一汉 家宫女孤身只影荒漠间;一步步,一回头,诉不尽生死别离胸中怨。这琴声,如梦似离,如吟似叹,勾魂引魄,低迴婉转;只觉得,魂牵梦绕,余音绕梁几日难尽; 方才知,人间何会有“感天地、泣鬼神”之放言。这便是闵慧芬二胡专辑《凤吟》的开篇:“昭君出塞”。
冷静之余,不觉心生思绪?余识二胡卅余载,又常以此业为生,听得看得的名人妙曲不下上百。少壮时,曾被不少名曲高手拨动心弦:或喜或悲、或怒或怨、或奇或 狂,而今已人过天命,凡事皆趋于平淡,很难再有被胡琴上的旧曲新调撩拨得寝食不宁。今又缘为何故,直发少年痴狂,是曲调的天籁之音,还是演奏的鬼使神功, 诱得久违了的情怀一任倾泻。
自此十日有余,便对这张光碟反复聆听,细细揣摩:“昭君出塞”中的凄美哀怨,“宝玉哭灵”里的世态悲凉,“打猪草”的两情相悦和“夜深 沉”的苍凉悲壮,一首首,透视着演奏者不凡功力,一幕幕,映象着人世间离合悲欢……这是一张二胡演奏的问鼎之作!一把胡琴,拉出了一个民族的人情和世情。
初识闵惠芬,仰慕于她的二胡技艺。那是卅五年前的中学阶段,大街小巷的广播喇叭里传出的二胡曲《喜送公粮》(顾武祥、孟津津曲)《红旗渠水绕太行》(闵惠 芬、沈利群编曲),充满着蓬勃朝气,激发我辈对二胡这件乐器的兴趣和向往。知青时期,如泣如诉的《江河水》(东北民间乐曲黄海怀移植),引领青少一族起早 贪黑,发奋苦练,手上的老茧剥了一层又一层,新买的唱片磨烂一张又一张,为的是追求那般“仇深似海”的二胡琴声。大学期间,又是那引人入胜的《新婚别》 (张晓峰曲),气势恢宏的《长城随想》(刘文金曲),诱得我等在二胡艺术的道路上不离不弃、无悔无怨。可以说,这种一代二胡人的“闵惠芬情结”,很有代表性意义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,闵惠芬的二胡艺术, 就像是二胡征程上的一座灯塔,激励着一代代人的二胡梦,照亮了一批批人的学琴路。她的才华和技艺,已深深融入了千千万万个后学的二胡生命之中,形成了持久 而深远的艺术影响力。
再识闵惠芬,折服于她的艺术佳境。如果说,当年江南水乡小镇湾斗里的那个小姑娘,对二胡的敏感和痴迷是出于天赋;青年时在全国大型二胡比赛中一举夺魁 是出于才华和技艺;中年时代名扬天下是由于突出的影响和贡献,那么,不惑之后的闵惠芬,其琴声由外放至内敛,由极致到从容,已出神入化,渐入佳境。从《江 河水》的人间悲切,到《洪湖心愿》的浩然正气;从《新婚别》的柔肠寸断,到《长城随想》的雄浑壮丽;从南音谐谑的《寒鸦戏水》(潮州筝曲,闵惠芬改 编),到北族狂放的《赛马》(黄海怀曲)一曲,闵氏琴韵,以穿越时空的超然魅力,演绎着一个民族的气质和魂魄。
又识闵惠芬,感怀于她的声腔琴风。20世纪的二胡艺术,群星璀璨,熠熠生辉,可歌可书的二胡名家不在少数,但依笔者之见,上个世纪二胡演奏艺术独树一帜、卓成大家的当属三人:阿炳、 蒋凤之和闵慧芬。这三位演奏大师各具特色的二胡琴风“说”“吟”“唱”,构成了20世纪二胡演奏艺术风格的三原色。相对于阿炳民间二胡琴风的 “说”,蒋凤之文人二胡风格的“吟”而言,闵氏二胡之所以脱颖而出,就在于她那无人能及的二胡之“唱”。这歌唱般淋漓酣畅的二胡琴风,应着六、七十年代时 代颂歌的需求,一经问世便一路高歌而势不可挡,成为20世纪下半叶二胡琴风的主流,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二胡演奏风格的行程。
闵氏琴风的二胡之“唱”,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早期的闵氏二胡,来自民歌和时调的滋养而多于“歌唱”,如《春诗》(钟义良曲)《红旗渠水绕太行》《洪湖人 民的心愿》(闵惠芬编曲)等;中期的闵氏琴风,是基于戏曲唱腔的浸润而长于“叙唱”,如《新婚别》《长城随想》《昭君出塞》《逍遥津》(京剧唱腔,闵惠芬 编曲)《宝玉哭灵》(越剧唱腔,闵惠芬编曲)等;那么,后期的闵氏二胡,则是在致力于汲取中国传统戏曲和民族音乐精华的基础上,而形成的“器乐演奏声腔 化”理念的追求。
关于闵惠芬声腔化二胡的命题,近年来学界多有研究。以己之见,闵氏二胡声腔化的本质,是开启了现代二胡的寻根之路,为二胡寻找那原本属于它的文化母体——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。
我们知道,乐器是文化的载体,一种乐器凝聚着一种文化的特质。在中国乐器的大家族里,相对于钟鼓里商周的厚朴,箫笛中汉晋的幽婉,琴筝上唐宋的铺饰而言,胡 琴类乐器,是伴着明清鲜活的地方百戏发展而来的。与箫笛、琴筝和琵琶相比,二胡更属于常民的乐器,它的前身,脱胎于中国地方戏曲伴奏、民间歌舞伴奏以及说 唱音乐伴奏。它的根脉深深扎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、戏曲和说唱之中,它的音韵抒发着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人世百态。草根性、地方性是二胡的文化母语。
近世二胡,不到百年的时间,已经从草根情结到文人意识,又从文人意识到民族象征,实现了其身份转变的三级跳。20世纪初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,近现代国乐先驱刘天华等 一批先贤,把二胡从贩夫走卒手中的一个“响器”,变成了登堂入室、走进高等学府的一件“乐器”;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之后,刘氏学派一代代传人的不懈 努力,又使二胡这件乐器,逐渐成为登临世界舞台、象征民族精神的一件“道器”。在二胡由“响器”成为“乐器”,由“伴奏时代”走上“独奏时代”的 行程中,独奏二胡极力摆脱着对声乐唱腔的依附,作着专业化、器乐化的努力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这种努力,在中外器乐发展史上,是一件乐器进化的必经之 路。
今天,在近现代中国西方化进程的走向之下,在时代变革、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态变异的大背景中,在中国音乐教育西方音乐课程体系的培育下,百年里程之二胡,已由世纪初刘天华先生的“调和之路”,逐渐走向了小提琴化、 钢琴化、交响化的“西化之旅”。二胡的音乐,已少见昨日乡风俚语之音律;二胡的琴风,也鲜有黎民百姓之语风。二胡的现状,在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的大语境 中,正沿着工业化、标准化、竞技化的道路一路前行,由此而引发在创作、演奏、教学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,深深引起了当今二胡界的思考和忧虑。 如此情境之下,重新理解闵惠芬“器乐演奏声腔化”的理念,就会认识到其中民族器乐文化本源的深层问题。它不仅体现了一位演奏家多年实践的真切感 悟,蕴含着一位艺术家为民族为大众的毕生追求,还凝聚着一个思想者的历史视野和艺术智慧。这种集一世之功修炼而成的艺术智慧,值得行走于竞技时代的二胡今 人深深思索。
……
在众多有关闵惠芬二胡艺术的研究之外,令笔者关注的,还有闵氏二胡中那不大被人谈起的两点神奇:即“女手男音”和“南人北曲”。
随 便翻开中外器乐演奏史,我们不难发现,由于女性演奏家和男性演奏家生理结构和性情气质多方面的不同,他们的演奏风格总会因性别差异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两大特 征。一般地,女性演奏家偏于纤巧细腻、含蓄柔婉之情;男性演奏家多于粗犷豪放、雄浑刚毅之气。而闵氏二胡的琴声,既有男性之胸怀,又含女性之情愫;既透出 一般男性所不长的精妙细润,又拥有一般女性所不及的气势磅礴。
此外,中国器乐的演奏史上,由于地域之别疆土之广,无论是古琴、古筝,还是箫笛、琵琶,很容易由于南北地理气候、语言习惯、性格爱好、风俗趣味的差异,而形 成南北风格不同的演奏派系。通常认为,南人偏重于清丽委婉的水灵之气,北人侧重于厚朴遒劲的山雄之风。而闵惠芬作为道地的苏南水乡人,又在毗邻东海的上海 就学成长,她的琴风却既有南人的秀美又有北人的豪放,特别是《长城》中坚如磐石的行弓,《新婚别》中柔肠百转的运指,迄今依然无人能及。可以说,闵氏二胡中“女手男音”和“南人北曲”的现象,不仅成为器乐演奏史上的一个鲜例,也会成为后人一时难以跨越的两个巅峰。
毋庸置疑,闵惠芬的二胡艺术,在中国二胡独奏时代从“乐器”走向”道器”的途中,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,她以自己的巾帼之躯,坚定的信念,执着的追求,始终走 在了二胡事业的最前列,一步步实现着刘天华及其传人“使二胡臻上品”的二胡之梦。她的演奏涉猎之广、受众之多、影响之大、艺术生命之强,给二胡史留下了一 个永久的传奇。